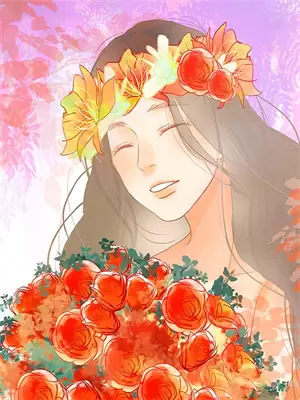
为支付母亲的巨额医疗费,我签下了地下陪拍协议。当我戴着遮脸面具跪在包厢时,
买主却用刀尖挑起我的下巴:“认识你九年,倒学会了当玩物。”刀锋割开面具的瞬间,
沈清言的冷笑冻结在脸上——三小时前拍卖会上,我偷拍的正是他天价拍下蓝钻的独家视频。
“林晚,你妈快死了就只会偷拍吗?”我笑着解开西装纽扣:“沈总,
我还学会更值钱的技能。”灯。像是无数淬火的针尖,毫不留情地扎进我的眼帘。
包厢厚重的门在我身后闭合,隔断了外面觥筹交错的嘈杂,只留下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
沉甸甸地压在空气里。
一股冰冷、干燥、带着昂贵烟草和某种我根本认不出名堂的皮革余烬混合的气息,
霸道地钻进鼻腔。每一个毛孔都警惕地张开了。视线所及,是沉郁浓重的暗红色天鹅绒墙布,
吸走了所有的暖意;脚下踩着的波斯地毯柔软得过分,
每一步都像踏在即将吞噬我的流沙之上,陷落的危机感如影随形。我垂着眼,
强迫自己的目光只落在脚下那一片繁复冰冷的地毯花纹上。“货真价实。
”一个声音在我前方响起,像结冰湖面下的暗流,平静,低沉,裹挟着足以致命的寒意,
毫无预兆地贯穿鼓膜,直直扎进我混乱的脑海深处。
这声音……带着某种被时光磨砺过却反而更加锐利的熟悉感,
甚至比记忆里那个总是带着温和笑意、会耐心帮我解题的少年嗓音更低醇一些,
但那核心的冷漠质地,却像一把陡然出鞘的冰刃,
瞬间将我所有刻意维持的冷静劈开了一道裂缝。我的心跳猝然错位,重重砸在肋骨上,
发出只有我自己能听见的空洞巨响。怎么可能?一只手伸了过来,
冷白的指节在刺眼的顶灯下显得有些透明。修长的手指,指甲修剪得极为干净利落,
此刻却毫不留情地捏住了我罩在脸上的、缀着细碎廉价水钻的化纤面具边缘。
那毫无温度的手指触碰到我下颌裸露皮肤的一刹那,一丝战栗无法控制地顺着脊椎飞速爬升。
紧接着——“嘶啦!”廉价的塑料面具撕裂的声音,在这空旷而安静得令人窒息的空间里,
尖锐得刺耳!灯光毫无遮挡地倾泻而下,彻底驱散了遮蔽,
也驱散了我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刺得我眼前瞬间一片空白。模糊的白光散开,
我终于看清了那张近在咫尺的脸。九年……那张记忆中尚带少年轮廓的脸庞,
如今线条已被岁月刻凿得清晰冷硬。鼻梁依旧高挺,唇线薄而锋利,
只是那弧度里再也寻不到一丝温润的笑意。最慑人的是那双眼睛,
深邃得像风暴前夕的死寂海域,此刻正沉沉地盯着我,
里面翻滚着极其复杂的情绪——汹涌的惊愕,似乎还有一丝……难以置信的狂怒?以及,
最深处,那浓得化不开的、冰冷的失望,如同深渊冻结了亿万年的寒冰,
瞬间将我血液的温度也一同带走了。沈清言。真的是他。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停顿、冻结。
包厢里的空气凝固了,沉重得如同铅块,挤压着胸腔,每一次微弱的呼吸都带着撕扯的痛感。
连顶灯那灼热的光线,都似乎失去了温度,只剩下冰冷的注视。“林晚?
”他几乎是咬着牙吐出这两个字,齿缝间溢出的寒气几乎冻结了空气,
“哈…呵…”短促的冷笑像是冰晶碎裂,锋利地砸下来,在死寂的包厢里反复撞响,
狠狠刮擦着我的耳膜。“认识你九年,”他声音的尾音诡异地上扬着,
带着某种被彻底戏弄的震怒和冰冷的嘲讽,“倒学会了……当玩物?”每一个字,
都像淬了毒的冰棱,精准无比地刺穿了我勉力维持的、如同纸糊一般的屏障,
深深扎进心脏深处最脆弱的地方,搅动起一片翻江倒海的羞耻与剧痛。
我能感觉到全身的血液在这一瞬间争先恐后地涌向双颊,灼烫得像是要燃烧起来,
但不过刹那,又被那眼神里冻结一切的冰冷狠狠抽干,
留下死灰般的麻木和遍布四肢百骸的寒意。指尖无法控制地颤抖着,指甲死死掐进手心软肉,
用那点尖锐的刺痛来换取一丝可怜的清醒。胃袋像被一只巨大的冰手攥住,拧紧,翻搅,
酸液汹涌地灼烧着喉管。视线无法控制地模糊了两次,又强迫自己狠狠眨回去,
倔强地、毫不退缩地迎上那双深渊般的眼睛。他眼里的惊怒,不解,
还有那刺骨的失望……像一把钝刀,在我的神经上来回拉扯。“沈总,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带着一种奇异的平稳,
仿佛这具麻木颤抖的躯壳里住着另一个失控的灵魂,连我自己都诧异于此刻的平静,
但每个音节都轻飘飘的,如同悬浮在这凝结的空气里,“真是……好久不见。
”这句客套像是触发了某个更危险的开关。沈清言猛地倾身靠近一步。
—混合着雪松凛冽的尾调和某种更沉稳的烟草余韵——再次裹挟着巨大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
但此刻,这气息里只剩下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和暴怒前夕的冰冷威压。他没有多余动作,
仅仅是这姿态的骤然改变,那股迫人的寒意就如冰河炸裂般冲击过来。他甚至没看我,
利地扫过我放在脚边的那个印着“伊维登拍卖行”Logo的硕大手提袋——袋口微微敞着,
里面专业镜头折射出的幽冷金属光泽,在灯下无所遁形。
一丝讽刺至极、比北极冰原深处风暴更寒冽的弧度,扭曲了他紧抿的薄唇。“呵!
”又是一声短促的冷笑,每一个音节都像淬了冰渣。“看来不光当了玩物,”他猛地扭回头,
那双深渊般的瞳孔死死锁住我,里面燃烧的不再是纯粹的怒意,
而是一种仿佛信仰被最卑劣谎言玷污后的、足以将灵魂彻底焚毁的冰冷火焰。
“还做起了肮脏的偷拍勾当?”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山岳崩摧前那种可怕的沉闷压力,
每一个字都狠狠敲打着房间的四壁,再反弹回击我的心脏。“林晚,”他身体再次前倾些许,
那冰冷的目光如同实质的利刃,把我钉在原地,声音低沉得如同磨砂纸在刮擦骨头,
字字清晰,又字字剜心,“九年,
一千零九十五万块钱……”他声音里压抑着惊涛骇浪的怒火,每一个数字都像淬毒的针,
“就让你妈教出这么个下作女儿?她躺在ICU里,需要钱续命,
你就只会像个阴沟里的耗子一样,”他的嗓音陡然拔高了一瞬,又死死压回危险的低沉,
“学会偷拍了,是不是?!”那个称呼,“耗子”,像淬毒的冰针,狠狠扎进耳膜。
母亲躺在监护仪冰冷的滴答声里挣扎的场景瞬间淹没了我。惨白的床单,紧闭的眼,
机规律却令人窒息的嘶鸣……和眼前这张被极致怒火扭曲的、曾经是我青春里唯一救赎的脸,
疯狂地交织、撕扯。所有小心翼翼在内心深处筑起的堤坝,在这一刻被冲垮了!
胸腔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轰”的一声爆开了!是某种绝望的熔岩,
裹挟着同样滚烫的耻辱和破釜沉舟的疯狂!我的目光不再闪躲。猛地抬起头,
对上他那双深不见底的怒眼。
脸上那些伪装性的麻木和不安被一种近乎燃烧的、扭曲的笑意悍然撕碎。嘴角向上拉扯着,
完全不受控制。笑容绽开的那一瞬,我感到自己脸颊的肌肉僵硬地绷紧,
牵扯出一种近乎诡异的线条。“呵……” 一声低笑从我喉间溢出,短促,干脆,
带着决绝的气息,像是在玻璃碴子上滚过。“沈总,您说得对。
”我的视线毫不退缩地迎向他锐利的目光,右手却动了。
动作甚至带上了一种不合时宜的优雅,如同舞蹈的开场。我缓缓抬起手,
越过胸前那枚碍眼的遮挡,
住了那枚光滑、冰冷、象征着束缚的黑色西装纽扣——扣眼里那根坚韧的丝线在我指尖绷紧,
传递着细微的阻力。我微微施力。“啪嗒。”一声轻响,微小得几乎被灯光融化,
却异常清晰地刺破了凝滞的空气。冰冷的纽扣弹开了,
垂悬的黑绳在我的动作下颤动出微弱的弧光。紧接着,我没有丝毫停顿。
手指像带着某种奇异的节奏,飞快地在其余纽扣上滑动。不需要看,
每一个位置都记得如此清晰。它们在我的指间依次发出细碎的、几乎被忽略掉的声响。
西装前襟如同被解除魔法的帷幕,迅速向两侧滑开、褪去,
彻底敞露出内里的景象——不是预想中低劣廉价的贴身吊带。取而代之的,
是一片冷冽、流畅,泛着高档合成面料特有微妙光泽的银灰色。
那是一个极有设计感的马甲式“内衬”,裁剪犀利,线条简洁,紧紧包裹着腰身,
勾勒出利落的轮廓。而在其肩带之上,
精巧地、牢靠地固定着一个闪烁着幽暗金属蓝光的高精度微型摄像机镜头,
镜头旁一枚不起眼的、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绿色指示灯,
此刻正稳定地散发着呼吸般微弱的光芒。“看啊,” 我的笑容扩大,嘴角的弧度愈发锋利,
声音轻得像一片薄刃刮过冰冷的空气,清晰地送入他耳中,
带着某种孤注一掷、玉石俱焚的坦然和挑衅,“……我还学会了更‘值钱’的技能。
”整个空间的空气瞬间被彻底抽空!针落可闻!灯光仿佛在这一刻也凝固了,
焦灼地烫在我脸上,又在沈清言骤然放大的瞳孔中反射出难以置信的冰蓝色光泽。
他脸上的每一丝表情,
那万年寒潭般深邃眼中翻腾的惊涛骇浪——先是如同高速摄影下镜头的急剧拉近,骤然收缩,
凝固,瞳孔深处掠过一丝极其清晰的震惊和错愕,
仿佛高速运行的精密机器被瞬间卡入了一枚致命的错误部件。
那失序的空白仅仅持续了电光石火的一瞬,便被更汹涌、更暴烈的情绪洪流瞬间吞噬!
那张五官深邃、向来掌控全局的英俊面孔上,
惊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裂开的缝隙里喷薄而出,
在他紧抿的唇线、绷紧的下颌、微微扩张的鼻翼上凝结成实质的冰霜与火焰!
我毫不退避地看着这一切在他脸上上演。时间在巨大的震惊中,似乎被无限拉长,
又被瞬间压缩。下一秒,世界重新恢复了令人心悸的冰冷。
沈清言脸上那短暂的、几乎失控的空白瞬间消失了。
仿佛惊鸿一瞥的裂痕被一种冷酷至极的铁灰色合金重新熔铸、弥合。没有暴怒的咆哮,
没有下一步的动作,刚才那股毁灭性的威压反而诡异地消失了。他只是微微退后了一步。
仅此一步。我们之间瞬间重新拉开了一臂的距离。
空气中那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像涨潮时的海水,“哗啦”一声骤然退去,
留下满地冰冷、死寂的滩涂。他高大的身形逆着水晶吊灯刺眼的光源,
边缘被勾勒出一道锋利冷硬的金边,像一尊骤然失去温度的青铜铸像。
灯光在他脸上投射下深邃、变幻的光影,那双眼睛彻底沉入了冰封之下的绝对死寂,
再无任何情绪波澜,
只剩下深不见底的一片冰原——广袤、单调、足以将一切情感冻结至彻底沉默的荒原。死寂。
比包厢之前任何一个瞬间都更要沉重、更要黏稠的死寂,如同万吨深海的压强,
无声无息地从四面八方合拢,挤压着我脆弱的胸骨,
每一次试图吸入的空气都像在撕扯冰冷的刀刃。
心脏在麻木之后开始剧烈地、毫无规律地撞动,像一头濒死的野兽在试图冲破它冰冷的囚笼。
我能清晰地听到血液在耳膜里奔突的声音,
和远处空调送风口极其微弱、几乎被彻底掩盖的“嘶嘶”气流声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这片绝对寂静里唯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背景音。恐惧的后劲,
那种从灵魂深处弥漫开来的寒意,此刻才慢半拍地、更猛烈地攥紧了我的五脏六腑。
我垂在身侧的手,指尖冰凉得失去了知觉。刚才那点豁出去的勇气,
像是耗尽火柴最后的光亮,此刻只余下颤栗的灰烬。但我依旧死死挺直着脊背,
维持着那个如同盔甲般冷硬的站姿,微抬的下颌没有丝毫松弛的迹象。双眼如同被焊住般,
依旧紧锁在他那双深不见底、映不出任何情绪的死寂眼眸里。“很好。”许久,
或者说只是须臾。一声如同碎冰砸落在金属台上的、极其清脆清晰的短音划破了死寂。
两个字,从沈清言薄如刀锋的唇间吐出,没有丝毫重量,却带着彻骨的寒意。那不是夸奖,
更不是接纳。那是宣判。是绞索收紧前冰冷的滑动。他紧锁在我脸上的目光,终于动了。
那冻结的冰原裂开了一道缝隙,目光如一道冰冷的射线,缓缓地、不带一丝温度地向下移动,
越过那件设计冷硬的银灰色“内衬”,
最终锁定在那个仍在忠诚工作、闪烁着稳定幽绿光点的微型摄像头上。那目光里既没有鄙夷,
也没有惊诧,有的只是一种审视工具的冷静打量,像是在评估一台机器的性能参数,
冰冷的目光在那金属镜筒上停留了一息。那毫无波澜的注视,
却比世上任何羞辱的言语都更令人如坠冰窟。仿佛被那目光实质性地刺痛,
又或许是终于完成了最后的确认,他猝然收回了视线。接着,
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没有再看我一眼。沈清言猛地转身。
动作利落得如同军人,又带着一股被强行压制、却依旧喷薄的怒火留下的余韵。
昂贵的黑色丝绒窗帘边缘在他擦身而过时,无风自动,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厢那扇沉重的、能将一切声音隔绝在外的漆黑实木门被他一手拉开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
他没有停顿,身影决绝地消失在门外。“砰!
”一声沉重得仿佛带着整个空间都在摇晃的撞击声!不是甩,而是砸。
实木门狠狠撞在门框上发出的巨大闷响,如同沉重的鼓槌敲打在心脏之上,
余音在密闭的空间里四壁震荡、嗡鸣,将我最后一丝力气也震得粉碎。门在他身后闭合。
隔绝了外面模糊不清的另一个世界,也隔绝了他。
徒留巨大的回声在空旷得过分的豪华包厢里独自咆哮、盘旋、最终无可奈何地消散,
只剩下彻底的、令人心慌的绝对死寂。
像是整艘巨轮最终沉没后海面上留下的巨大涡流和空洞。他走了。就这样,走了。
没有预想中的暴怒、质问、砸毁……什么都没有。仅仅是那一声砸门的巨响,
反而如同最锋利的冰锥,扎穿了心脏表面那层勉力维持的、自欺欺人的铠甲。
恐惧失去了目标,却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一种更加粘稠的、深入骨髓的凉意,
沿着裸露的皮肤迅速蔓延开来。我挺得笔直的脊背终于无法支撑,轻轻一颤。
支撑着我的那股“气”,被那一声巨响彻底抽干了。所有的伪装,所有强行撑起的骨架,
都在这一瞬间如同被白蚁蛀空的朽木般轰然坍塌!腿上仿佛瞬间被抽掉了所有骨头,
软绵绵的酸胀感如同潮水般涌起。身体再也无法维持那个孤傲挺拔的姿态,晃了一下,
又一下。终于,膝盖如同被无形的重锤砸中,再也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
软软地向铺着繁复冰冷花纹的地毯跪了下去。丝绸质感的马甲料子滑腻地蹭过皮肤,
带来一阵不寒而栗的冰冷触感。膝盖接触柔软地毯的瞬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地面沉没的接纳反而像一个恶意的提示——提醒着我此刻的狼狈与不堪。
如同被彻底剥光了所有伪装,赤裸裸地暴露在寒流之中。我跪坐在这片昂贵的寂静里。
头顶那庞大华丽的水晶吊灯,无数切割完美的棱面依旧冷酷地折射着璀璨得近乎虚无的光芒,
将整个包厢照得如同白昼,











